大一统的“传播权”及其制度构建
 2021-01-30 15:01:03|
2021-01-30 15:01:03| 256|
256| 起点商标网
起点商标网 提出大一统的“传播权”之构想并非笔者异想天开。这种观点在国外已经被提议过。澳大利亚版权法审议委员会曾于1999年2月公布了一份题为《简化1968年版权法》的报告,建议大幅度简化澳大利亚现行版权法中关于作品分类、版权人专有权等法律规定。报告建议将版权人的专有权简化为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权两种。〔1〕这种大一统的“传播权”,应当是一般意义上的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不具有客体的特定性(specifc)和传播方式的具体规定性。〔2〕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涉及版权的行为,传播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多种使用方式。可以说,传播行为本身就涉及多种版权权项的重合。
我国有学者分析认为,现行《著作权法》下的版权各权项均可从传播权出发得以表达,并从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进行剖析。在人身权方面,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可由传播权一体保护,“发表”本身就属于传播行为之一种,因此“传播权”便已涵盖“发表权”,未经权利人同意之发表行为必然侵犯“传播权”;“署名”、“修改”只有作为“传播”的前期准备行为方具备法律规制的意义,若不进行“传播”,“署名”和“修改”丝毫无损于著作权人的利益,无须法律加以规制。在财产权方面,著作财产权的各项权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权能所规制之行为实为“传播的前期准备行为”,包括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第二类是“具体的传播行为”,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类是权能所规制之行为乃是“具有传播性的行为”,如发行权。
我国学者在以往论述中也曾使用“传播权”这一用语。但是,由于传播权并非立法用语,学者们在论述传播权时,呈现出见仁见智的现象。王迁教授认为,在著作财产权体系中,有一类权利被称为“公开传播权”,它控制的是以不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使公众得以欣赏或使用作品内容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属于“公开传播权”的专有权利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展览权五项权利。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发行权和出租权虽然也使公众获得了作品,但却是以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方式进行的,因此,发行权和出租权并不属于“公开传播权”。〔4〕梅术文也建议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划分为复制权、传播权和演绎权,
传播权具体又包括表演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该作者在之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修正,认为传播权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五种形式。概言之,此类观点认为,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所享有的在不转移作品载体的前提下,向不特定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从而排除了发行权和出租权。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持此说法。郑成思教授认为:“版权中的经济权利可分为复制权、演绎权与传播权三大类......发行权、播放权、表演权、展览权等等属于传播权的经济权利......”。吴汉东教授等的《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也认为:“著作财产权主要包括三类权利:财产权、演绎权和传播权......公演权、广播权、朗诵权、发行权、放映权、有线转播权、出租权、展览权等皆与作品的传播有关,统属于传播作品的权利”。卢海军曾建议将著作权分为复制权、传播权、演绎权、其他权利等四个种类,其中,传播权又包括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这类观点明确地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传播权的范围。
以上两类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传播权。以我国法律规定为例考察,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发行权指的是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出租权指的是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笔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是一种传播,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等也是一种传播。应当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大一统的传播权范畴之下。尽管发行权建立在复制权基础上,需要以提供原件或复制件为前提,但通过发行权的行使,静态的复制行为已经变成动态的传播行为。
以我国法律为例,版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版权包括下列财产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不难发现,财产权中的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七个权项的共同特性非常明显,即具有“公开性”和“公众性”,完全可以在这七个权项之上建立一个上位概念“传播权”。
有人也许会担忧,如果打破现有列举模式,建立“表演权”、“广播权”、“放映权”和“展览权”等权利的上位概念“向公众传播权”,会使原有的并列列举式立法变得混乱。孰不知,原来的并列列举式立法已经存在混乱,比如放映权实质上是一种机械表演,有了表演权,再规定放映权从逻辑上是多余的。又如翻译权、广播权这些权项,对美术作品、建筑作品毫无适用之处。现行立法可能会给我们强加一种习惯思维,似乎现行立法就是合理的,去改变它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思维是有失偏颇的。
实际上,有些国家的立法早已使用概括的、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版权中的财产权都是予以“开放式”的规定。典型的如法国1992年《知识产权法典》规定著作权人主要享有两种概括的权利,即表演权(le droit de représentation)和复制权(le droit de reproduction)。法国的表演权包括以任何方式将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涵相当于本书所谓的“传播权”。类似地,荷兰法律也规定概括的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权。荷兰《版权法》第一条规定:“版权是文学、科学或艺术作品的作者或其继承人就那件作品向公众传播和复制(reproduce)的排他性权利。”该法第四节和第五节分别对这两大类权利进一步作了规定。在这些广泛的财产权之下,这些国家的法律以更具体的方式规定其中内容。“开放式”的权利立法模式的特点
是其中规定的具体权项只是以例子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穷尽式的列举。
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之目的并非在于其本身。“从概念到制度”,需要进一步地予以制度构建。整合和简化传播权的核心功能是突出传播权在版权的权项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整合之后的特具包容性的传播权之地位将更加突出。相对于复制权而言,将传播权提升为版权制度的中心也成为一种符合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的选择。
在整合和简化传播权概念之后,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制度的关键之一是进一步规定“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作品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这种观点是合理的。比如,张三偷偷地把韩寒写的《三重门》自己复印一份,但这本复印件一直放在他抽屉里,未被任何其他任何人发现,难道这也要追究张三侵权复制权的责任吗?其实这也无法追究,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其复制了此书。其实这一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扩张,如“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翻译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现实中也是如此,如李四为了锻炼翻译能力自己翻译一本英文著作,但未将之以任何形式公开,难道这也要征得原作者同意吗?考虑到目前最迫切地是解决“复制”难题,本书将核心观点仅限于“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至于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其他静态的权项实际上也可类推适用。
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及进而的制度构建,不仅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面临的临时复制、私人复制等问题,还可以较好地适应未来技术的发展。灵活的、技术中立的权利可以包括现在尚无法预见的行为。概言之,本书所提议的“传播权”并非我国立法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是WCT中的“向公众传播权”,而是一种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本章试图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知识产权的激励功能等理论角度对“传播权”作为版权的中心进行辨析,并提出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制度之具体构想。笔者建议在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七个权项之上建立一个上位概念“传播权”,并进而规定“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可以得到论证。大一统的“传播权”制度在解决临时复制、私人复制等难题时可以起到良好效果,也可以跳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交互性与否的争论,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难题。
“传播权”作为版权之中心的学说在国内外早已有之,但对其的论证尚远远不够,这是一项有必要继续进行的工作。笔者进行初步论证,抛砖引玉,希冀更多学者关注这一变革性、前瞻性的命题。
我国有学者分析认为,现行《著作权法》下的版权各权项均可从传播权出发得以表达,并从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进行剖析。在人身权方面,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可由传播权一体保护,“发表”本身就属于传播行为之一种,因此“传播权”便已涵盖“发表权”,未经权利人同意之发表行为必然侵犯“传播权”;“署名”、“修改”只有作为“传播”的前期准备行为方具备法律规制的意义,若不进行“传播”,“署名”和“修改”丝毫无损于著作权人的利益,无须法律加以规制。在财产权方面,著作财产权的各项权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权能所规制之行为实为“传播的前期准备行为”,包括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第二类是“具体的传播行为”,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类是权能所规制之行为乃是“具有传播性的行为”,如发行权。
我国学者在以往论述中也曾使用“传播权”这一用语。但是,由于传播权并非立法用语,学者们在论述传播权时,呈现出见仁见智的现象。王迁教授认为,在著作财产权体系中,有一类权利被称为“公开传播权”,它控制的是以不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使公众得以欣赏或使用作品内容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属于“公开传播权”的专有权利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展览权五项权利。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发行权和出租权虽然也使公众获得了作品,但却是以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方式进行的,因此,发行权和出租权并不属于“公开传播权”。〔4〕梅术文也建议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划分为复制权、传播权和演绎权,
传播权具体又包括表演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该作者在之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修正,认为传播权包括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五种形式。概言之,此类观点认为,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所享有的在不转移作品载体的前提下,向不特定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从而排除了发行权和出租权。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持此说法。郑成思教授认为:“版权中的经济权利可分为复制权、演绎权与传播权三大类......发行权、播放权、表演权、展览权等等属于传播权的经济权利......”。吴汉东教授等的《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也认为:“著作财产权主要包括三类权利:财产权、演绎权和传播权......公演权、广播权、朗诵权、发行权、放映权、有线转播权、出租权、展览权等皆与作品的传播有关,统属于传播作品的权利”。卢海军曾建议将著作权分为复制权、传播权、演绎权、其他权利等四个种类,其中,传播权又包括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这类观点明确地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传播权的范围。
以上两类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传播权。以我国法律规定为例考察,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发行权指的是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出租权指的是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笔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是一种传播,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等也是一种传播。应当将发行权和出租权列入大一统的传播权范畴之下。尽管发行权建立在复制权基础上,需要以提供原件或复制件为前提,但通过发行权的行使,静态的复制行为已经变成动态的传播行为。
以我国法律为例,版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版权包括下列财产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不难发现,财产权中的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七个权项的共同特性非常明显,即具有“公开性”和“公众性”,完全可以在这七个权项之上建立一个上位概念“传播权”。
有人也许会担忧,如果打破现有列举模式,建立“表演权”、“广播权”、“放映权”和“展览权”等权利的上位概念“向公众传播权”,会使原有的并列列举式立法变得混乱。孰不知,原来的并列列举式立法已经存在混乱,比如放映权实质上是一种机械表演,有了表演权,再规定放映权从逻辑上是多余的。又如翻译权、广播权这些权项,对美术作品、建筑作品毫无适用之处。现行立法可能会给我们强加一种习惯思维,似乎现行立法就是合理的,去改变它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思维是有失偏颇的。
实际上,有些国家的立法早已使用概括的、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版权中的财产权都是予以“开放式”的规定。典型的如法国1992年《知识产权法典》规定著作权人主要享有两种概括的权利,即表演权(le droit de représentation)和复制权(le droit de reproduction)。法国的表演权包括以任何方式将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涵相当于本书所谓的“传播权”。类似地,荷兰法律也规定概括的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权。荷兰《版权法》第一条规定:“版权是文学、科学或艺术作品的作者或其继承人就那件作品向公众传播和复制(reproduce)的排他性权利。”该法第四节和第五节分别对这两大类权利进一步作了规定。在这些广泛的财产权之下,这些国家的法律以更具体的方式规定其中内容。“开放式”的权利立法模式的特点
是其中规定的具体权项只是以例子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穷尽式的列举。
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之目的并非在于其本身。“从概念到制度”,需要进一步地予以制度构建。整合和简化传播权的核心功能是突出传播权在版权的权项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整合之后的特具包容性的传播权之地位将更加突出。相对于复制权而言,将传播权提升为版权制度的中心也成为一种符合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的选择。
在整合和简化传播权概念之后,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制度的关键之一是进一步规定“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作品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这种观点是合理的。比如,张三偷偷地把韩寒写的《三重门》自己复印一份,但这本复印件一直放在他抽屉里,未被任何其他任何人发现,难道这也要追究张三侵权复制权的责任吗?其实这也无法追究,因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其复制了此书。其实这一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扩张,如“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翻译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现实中也是如此,如李四为了锻炼翻译能力自己翻译一本英文著作,但未将之以任何形式公开,难道这也要征得原作者同意吗?考虑到目前最迫切地是解决“复制”难题,本书将核心观点仅限于“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至于复制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其他静态的权项实际上也可类推适用。
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及进而的制度构建,不仅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面临的临时复制、私人复制等问题,还可以较好地适应未来技术的发展。灵活的、技术中立的权利可以包括现在尚无法预见的行为。概言之,本书所提议的“传播权”并非我国立法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是WCT中的“向公众传播权”,而是一种大一统的“传播权”概念。本章试图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知识产权的激励功能等理论角度对“传播权”作为版权的中心进行辨析,并提出以“传播权”为中心的版权制度之具体构想。笔者建议在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七个权项之上建立一个上位概念“传播权”,并进而规定“不具有公开性质、不侵犯传播权的复制是版权侵权的一种例外”,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可以得到论证。大一统的“传播权”制度在解决临时复制、私人复制等难题时可以起到良好效果,也可以跳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交互性与否的争论,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时代的版权保护难题。
“传播权”作为版权之中心的学说在国内外早已有之,但对其的论证尚远远不够,这是一项有必要继续进行的工作。笔者进行初步论证,抛砖引玉,希冀更多学者关注这一变革性、前瞻性的命题。
起点商标作为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产交易信息请点击 【在线咨询】或添加微信 【19522093243】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此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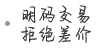
 商标分类
商标分类  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