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坚等诉彭某、某文艺出版社侵犯翻译作品著作权案
 2021-01-29 15:01:19|
2021-01-29 15:01:19| 246|
246| 起点商标网
起点商标网 案例概述
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四人系前苏联作家瓦连京·奇金所著《马克思的自白》一书的中文译者。该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字数114千字,印数112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0.51元。彭某于1989年也翻译了《马克思的自白》。该译本由华龄出版社1990年出版。
××年12月,被告彭某(甲方)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乙方)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约定由乙方出版彭某翻译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合同约定如发生侵权情况,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译者的稿酬为该图书的定价乘以9%(版税率)乘以销售数。该合同签订后,某文艺出版社于××年3月1日出版了该书,全书字数186千字,印数5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10元。××年1月,某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印数5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10元。某文艺出版社已将全部稿酬支付给彭某。
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年11月11日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进行鉴定工作,对蔡兴文及彭某在《马克思的自白》原著正文部分中的b、d部分各选择2段俄文原文进行了翻译。××年12月30日,鉴定完成,三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果(新译文)均无异议,均承认鉴定人员翻译的译文与蔡译本和彭译本的相关部分的译文存在较大差别。
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四人是《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中文版的译者,并于198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1989年,被告彭某在原告译本的基础之上采用变换词句等手法,将原告的翻译作品改头换面后在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礼道歉、停止侵权,各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被告彭某辩称:其多年从事俄文翻译工作,1989年有人请被告翻译前苏联作家瓦连京·奇金的作品《马克思的自白》。被告在翻看原告的译作时发现其中有多处错误,即着手进行了翻译,于1989年底完成,1990年在华龄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的自白》,后又于××年在某文艺出版社再版。原告的译本存在多处错误,被告未抄袭原告的作品,也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被告某文艺出版社辩称:该社于××年与译者彭某签订了出版合同,在取得其授权的情况下再版了《马克思的自白》一书,合同中约定如有侵权情况,由彭某承担一切责任,故该社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等四原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前苏联公民瓦连京·奇金的俄文作品《马克思的自白》进行中文翻译(蔡兴文等四人的译本以下简称为“蔡译本”),该行为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该中译本的著作权应归四原告享有。彭某有权对《马克思的自白》俄文本进行复译(对彭某的译本以下简称为“彭译本”),但在复译过程中,彭某接触到了蔡译本,这种接触限制了彭某独立创作思想的发挥,导致了两个译本在全书部分内容(所用词汇、文句结构)上的相同或相似,这种结果并不是基于彭某本人的智力创造工作。鉴于彭某并未取得原告的许可,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对其译作享有的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故彭某应停止侵权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某文艺出版社在知道蔡译本存在以及彭某接触过蔡译本的情况下,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的调查工作即出版发行了彭某的译本,完成了侵权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该行为也构成侵权。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无效。因原告方对其要求两被告各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再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理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八)项做出判决:
(1)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无效,被告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停止侵权;
(2)被告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向原告书面致歉;
(3)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
(1)四原告对其翻译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不享有著作权,因为四原告对该书的翻译未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因接触到前译本而受到影响,限制了独立创作,导致了两个译本中部分内容的相同或相似,从而构成侵权,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两个译本均来源于原著,而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著,所以,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包括词汇、文字、结构等方面,就必然存在着相同或相似;
其次,双方译者都是中国人,年龄相仿,生活的年代、环境相类似,其俄文和中文水平虽不相同,但用中文进行表达的规律和习惯,却要符合所处时代,所以两个译本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同或相似。
(3)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蔡译本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之前,确曾翻看过蔡译本,当时发现错误甚多,才重新进行翻译。
(4)一审判决认定“三方当事人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鉴定结果均无异议,均承认与蔡译本及彭译本存在较大差异”,与事实不符。
(5)一审判决认定“蔡译本与彭译本相对比,正文部分共有68处内容相同或相似”,与事实不符。
首先,两个译本正文部分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是事实,但并非是68处,关键是看什么部分相同或相似;
其次,如果说内容相同或相似,应该说全书都是,因为两本译作均来源于原作,内容就应该相同。
(6)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指控上诉人抄袭、剽窃构成侵权,一审判决对此未做评价,这实际上否定了抄袭、剽窃的指控。一审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八)项进行判决,实际上是对该项内容进行了解释,而一审法院并非有权解释的机关,其适用该条第(八)项判决,显属不当。
(7)一审判决判定复译只要与前译相同或相似,只要复译者不能证明没有接触过前译,就构成了侵权,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袁坚、孙维韬、韩维、蔡兴文,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均同意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等四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俄文版《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因《著作权法》尚未颁布实施,我国也未加入有关著作权的国际公约,故要求其在翻译之前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没有法律依据。蔡兴文等四人对该书的翻译行为,并未违反我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其对《马克思的自白》中译本享有的著作权,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
同样,彭某在1989年也有权对俄文版《马克思的自白》一书进行重新翻译。彭某在对该书进行翻译之前甚至在翻译之中,有权阅读其他译本,但对于自己的译本,其应该依据自身具有的专业知识,独立地进行翻译,不得在文字表现形式上抄袭他人的译本。对本案涉及的《马克思的自白》的蔡译本及彭译本中文字表达相同或近似的部分,除了共同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部分外,彭某没有提供其余部分是其独立翻译的证据。因此,应认定这些部分彭某抄袭了蔡译本。对于蔡译本及彭译本,因均来源于同一原著,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而两个译本内容上的相同,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因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作品的具体内容。就翻译作品而言,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该作品的句法结构、选词造句等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同一原著,不同翻译者若进行独立的翻译,由此产生的不同翻译作品在整体的表现形式上必然是不同的,这是一种翻译常识。所以,上诉人对蔡译本及彭译本在文字表达上存在的相同或相似所做的解释,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依据彭某在其答辩状中的自认,认定其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过程中阅读了蔡译本,并无不当。况且,彭某究竟是在翻译该书之前还是在翻译过程之中阅读了蔡译本,对本案的侵权认定问题并不产生实质影响。
对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所做的鉴定,彭某已于××年12月18日明确表示没有异议。北京外国语大学对相关段落的翻译与蔡译本及彭译本在文字表达上有较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审期间彭某对此反悔,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某文艺出版社在出版《马克思的自白》彭译本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其行为也构成侵权,应与彭某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无效,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对此,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虽认定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侵权,但并未查明抄袭部分的具体字数,只认定了在正文部分有68处内容相同或近似,另外有22条注释内容相同或近似。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此认定均有异议。因此,彭某的第五条上诉理由,部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承担的赔偿数额过高,对此,二审法院将依据二审期间查明的在文字表达上彭某抄袭蔡译本的具体字数,确定其与某文艺出版社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彭某的行为应属抄袭行为,一审法院适用了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第(八)项的规定显属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关于复译问题,复译本身并不侵权。但是,如果复译本与前译本在具有独创性的翻译文字表达上相同或近似,而复译者又接触过前译本,且其对此种相同或近似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复译者的行为应构成侵权。
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做出判决:
(1)变更一审第(1)项为被告彭某、某文艺出版社停止侵犯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著作权的行为;
(2)变更一审判决第(2)项为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向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书面致歉;
(3)变更被告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经济损失4452元。
案例评析
(1)本案原告的翻译作品的著作权是否存在瑕疵。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蔡兴文等四原告于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前苏联公民瓦连京·奇金所著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并未取得原作者的授权。对于未经授权而翻译产生的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法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译者没有得到原作者授权而进行翻译所产生作品的著作权本身就具有瑕疵,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未经原作者授权擅自翻译其作品(排除合理使用的情况)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译者没有取得原作者的授权,其翻译的作品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他人不得侵犯。理由是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是保护人类的无形的智力成果。虽然未经授权而产生的译作著作权的行使会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但其仍是人类的智力成果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合理使用的角度去考虑,无论是否得到原作者的授权,翻译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侵权。基于这种考虑,未获得授权的翻译作品的著作权仍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至于该翻译作品在行使其著作权时对原作著作权的侵犯,应由原作作者来向翻译者主张权利。
对于未经原作作者授权而翻译的作品的著作权是否有瑕疵,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提出在我国应适用三段划分法,这是较科学的。1991年6月1日,《著作权法》施行之前为第一时间段。彼时,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外国人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公民可以不经许可翻译外国作品而享有该翻译作品的著作权。本案即涉及此时间段。蔡兴文等四人对《马克思的自白》一书的翻译及出版,彭某对同一俄文作品的翻译及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均处于这一时间段。虽然蔡兴文等四人和彭某均未取得俄文原著作者的授权,但如果这两种译本之间不存在侵权关系的话,就均应享有翻译作品的完整的著作权。《著作权法》施行后至我国参加有关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前为第二时间段。我国《著作权法》并不是对所有外国作品都给予保护。该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而我国在1991年6月1日《著作权法》开始施行时尚未与他国签订过保护著作权的双边协议,也没有参加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直至1992年10月15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时《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款才真正具有司法上的意义。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时间差的出现。虽说只有短短的16个半月的时间,但如果一位译者在这一时间段未经外国原作者授权而翻译的作品之著作权是没有瑕疵的。1992年10月15日之后的时间为第三时间段,凡与我国同为有关保护著作权国际公约的成员国或与我国有相关的双边协议的国家的公民的作品,均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2)对于针对同一部外文作品而产生的两部翻译作品之间是否存在著作权侵权应如何认定。对同一部外文作品有两个甚至三个以上不同的中文译本是很常见的,比如,朱生豪和梁实秋就都曾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如果两位译者对同一外文作品各自独立进行翻译,两种译本之间就不会存在侵权的情况。由于翻译作品是以原作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演绎作品,不同的译者针对同一原作进行翻译,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应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不同译者的水平、翻译习惯、对原作的理解不同,在译文上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必然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在对彭译本和蔡译本进行鉴定时,鉴定人员独立翻译了部分《马克思自白》的原文,其译文与原、被告的译本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排除了译文是原作的“惟一表达形式”的可能,故独立创作的译文是具有独创性的,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对于不同译者的作品而言,翻译讲究“信、达、雅”,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在“信”这一层面上,针对同一外文作品的两部译作应该是区别不大的。而且《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是作品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能仅凭后译与前译在内容上的相同或近似就判断后译抄袭了前译,对前译构成著作权侵权。《著作权法》对作品外在形式的保护,具体到翻译作品而言,就是保护该作品的遣词造句,句法结构的形式等,即所谓“信、达、雅”中的“达”和“雅”的层面。译者的翻译水平,语言特色以及创造性劳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但判断后译作品对前译作品是否构成抄袭,不能仅凭某些词语句式上的相同或相似来认定。由于前译后译均来源于原作,很多词语和句式在上下文所限制的特定的语境中只能做一种解释,一种译法。具体到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值得注意。蔡译本与彭译本相比,在文字表达上共有162处相同或相似,可分为五类:
一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有30处;
二是部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由译者翻译15处;
三是短语2处;
四是完全由译者翻译共69处;
五是46条注释。
对于上述双方共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原文的部分,是不能认定为抄袭的。不同译者在对同一部西方作品进行翻译时,此问题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对原文中所引用《圣经》中的语言的翻译。虽然《圣经》的中译本版本很多,但如果两位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中所引述的《圣经》上的语言时,恰好参考的是相同的《圣经》中译本的话,就不能因为这部分译文的相同或相似而认定后译者对前译者进行了抄袭。在对后译作品是否抄袭了前译作品的判定中,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可能接触前译著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具体到我们正在探讨的个案,认定彭译本对蔡译本进行了部分抄袭,必须有彭某在翻译过程中接触过蔡译本的证据,但又不能仅凭接触而认定抄袭,彭某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有权阅读参考其他译本,包括蔡译本。在具备了有可能接触这一必要条件后,还要有其他证据在案佐证才可以认定抄袭事实的存在。在本案中彭某对其译本中排除了共同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部分外,仍有约23000字的内容与蔡译本文字表达相同或相似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再加上翻译过程中彭某接触过蔡译本的事实,就可以认定抄袭事实的存在。
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四人系前苏联作家瓦连京·奇金所著《马克思的自白》一书的中文译者。该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字数114千字,印数112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0.51元。彭某于1989年也翻译了《马克思的自白》。该译本由华龄出版社1990年出版。
××年12月,被告彭某(甲方)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乙方)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约定由乙方出版彭某翻译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合同约定如发生侵权情况,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译者的稿酬为该图书的定价乘以9%(版税率)乘以销售数。该合同签订后,某文艺出版社于××年3月1日出版了该书,全书字数186千字,印数5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10元。××年1月,某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印数5000册,每本定价人民币10元。某文艺出版社已将全部稿酬支付给彭某。
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年11月11日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进行鉴定工作,对蔡兴文及彭某在《马克思的自白》原著正文部分中的b、d部分各选择2段俄文原文进行了翻译。××年12月30日,鉴定完成,三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果(新译文)均无异议,均承认鉴定人员翻译的译文与蔡译本和彭译本的相关部分的译文存在较大差别。
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四人是《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中文版的译者,并于198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1989年,被告彭某在原告译本的基础之上采用变换词句等手法,将原告的翻译作品改头换面后在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二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礼道歉、停止侵权,各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被告彭某辩称:其多年从事俄文翻译工作,1989年有人请被告翻译前苏联作家瓦连京·奇金的作品《马克思的自白》。被告在翻看原告的译作时发现其中有多处错误,即着手进行了翻译,于1989年底完成,1990年在华龄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的自白》,后又于××年在某文艺出版社再版。原告的译本存在多处错误,被告未抄袭原告的作品,也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被告某文艺出版社辩称:该社于××年与译者彭某签订了出版合同,在取得其授权的情况下再版了《马克思的自白》一书,合同中约定如有侵权情况,由彭某承担一切责任,故该社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等四原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前苏联公民瓦连京·奇金的俄文作品《马克思的自白》进行中文翻译(蔡兴文等四人的译本以下简称为“蔡译本”),该行为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该中译本的著作权应归四原告享有。彭某有权对《马克思的自白》俄文本进行复译(对彭某的译本以下简称为“彭译本”),但在复译过程中,彭某接触到了蔡译本,这种接触限制了彭某独立创作思想的发挥,导致了两个译本在全书部分内容(所用词汇、文句结构)上的相同或相似,这种结果并不是基于彭某本人的智力创造工作。鉴于彭某并未取得原告的许可,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对其译作享有的使用权及获得报酬权,故彭某应停止侵权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某文艺出版社在知道蔡译本存在以及彭某接触过蔡译本的情况下,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的调查工作即出版发行了彭某的译本,完成了侵权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该行为也构成侵权。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无效。因原告方对其要求两被告各赔偿2万元经济损失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再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理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八)项做出判决:
(1)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无效,被告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停止侵权;
(2)被告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向原告书面致歉;
(3)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
(1)四原告对其翻译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不享有著作权,因为四原告对该书的翻译未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因接触到前译本而受到影响,限制了独立创作,导致了两个译本中部分内容的相同或相似,从而构成侵权,此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两个译本均来源于原著,而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著,所以,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包括词汇、文字、结构等方面,就必然存在着相同或相似;
其次,双方译者都是中国人,年龄相仿,生活的年代、环境相类似,其俄文和中文水平虽不相同,但用中文进行表达的规律和习惯,却要符合所处时代,所以两个译本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同或相似。
(3)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蔡译本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一书之前,确曾翻看过蔡译本,当时发现错误甚多,才重新进行翻译。
(4)一审判决认定“三方当事人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鉴定结果均无异议,均承认与蔡译本及彭译本存在较大差异”,与事实不符。
(5)一审判决认定“蔡译本与彭译本相对比,正文部分共有68处内容相同或相似”,与事实不符。
首先,两个译本正文部分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是事实,但并非是68处,关键是看什么部分相同或相似;
其次,如果说内容相同或相似,应该说全书都是,因为两本译作均来源于原作,内容就应该相同。
(6)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指控上诉人抄袭、剽窃构成侵权,一审判决对此未做评价,这实际上否定了抄袭、剽窃的指控。一审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八)项进行判决,实际上是对该项内容进行了解释,而一审法院并非有权解释的机关,其适用该条第(八)项判决,显属不当。
(7)一审判决判定复译只要与前译相同或相似,只要复译者不能证明没有接触过前译,就构成了侵权,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不良后果。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袁坚、孙维韬、韩维、蔡兴文,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均同意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等四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俄文版《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因《著作权法》尚未颁布实施,我国也未加入有关著作权的国际公约,故要求其在翻译之前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没有法律依据。蔡兴文等四人对该书的翻译行为,并未违反我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其对《马克思的自白》中译本享有的著作权,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
同样,彭某在1989年也有权对俄文版《马克思的自白》一书进行重新翻译。彭某在对该书进行翻译之前甚至在翻译之中,有权阅读其他译本,但对于自己的译本,其应该依据自身具有的专业知识,独立地进行翻译,不得在文字表现形式上抄袭他人的译本。对本案涉及的《马克思的自白》的蔡译本及彭译本中文字表达相同或近似的部分,除了共同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部分外,彭某没有提供其余部分是其独立翻译的证据。因此,应认定这些部分彭某抄袭了蔡译本。对于蔡译本及彭译本,因均来源于同一原著,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而两个译本内容上的相同,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因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作品的具体内容。就翻译作品而言,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该作品的句法结构、选词造句等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同一原著,不同翻译者若进行独立的翻译,由此产生的不同翻译作品在整体的表现形式上必然是不同的,这是一种翻译常识。所以,上诉人对蔡译本及彭译本在文字表达上存在的相同或相似所做的解释,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依据彭某在其答辩状中的自认,认定其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过程中阅读了蔡译本,并无不当。况且,彭某究竟是在翻译该书之前还是在翻译过程之中阅读了蔡译本,对本案的侵权认定问题并不产生实质影响。
对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所做的鉴定,彭某已于××年12月18日明确表示没有异议。北京外国语大学对相关段落的翻译与蔡译本及彭译本在文字表达上有较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二审期间彭某对此反悔,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某文艺出版社在出版《马克思的自白》彭译本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其行为也构成侵权,应与彭某承担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无效,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对此,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虽认定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侵权,但并未查明抄袭部分的具体字数,只认定了在正文部分有68处内容相同或近似,另外有22条注释内容相同或近似。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此认定均有异议。因此,彭某的第五条上诉理由,部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彭某及某文艺出版社承担的赔偿数额过高,对此,二审法院将依据二审期间查明的在文字表达上彭某抄袭蔡译本的具体字数,确定其与某文艺出版社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彭某的行为应属抄袭行为,一审法院适用了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第(八)项的规定显属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关于复译问题,复译本身并不侵权。但是,如果复译本与前译本在具有独创性的翻译文字表达上相同或近似,而复译者又接触过前译本,且其对此种相同或近似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复译者的行为应构成侵权。
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做出判决:
(1)变更一审第(1)项为被告彭某、某文艺出版社停止侵犯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著作权的行为;
(2)变更一审判决第(2)项为被告彭某与被告某文艺出版社向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书面致歉;
(3)变更被告彭某与某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原告蔡兴文、袁坚、孙维韬、韩维经济损失4452元。
案例评析
(1)本案原告的翻译作品的著作权是否存在瑕疵。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蔡兴文等四原告于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前苏联公民瓦连京·奇金所著的《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并未取得原作者的授权。对于未经授权而翻译产生的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法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译者没有得到原作者授权而进行翻译所产生作品的著作权本身就具有瑕疵,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未经原作者授权擅自翻译其作品(排除合理使用的情况)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译者没有取得原作者的授权,其翻译的作品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他人不得侵犯。理由是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是保护人类的无形的智力成果。虽然未经授权而产生的译作著作权的行使会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但其仍是人类的智力成果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合理使用的角度去考虑,无论是否得到原作者的授权,翻译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侵权。基于这种考虑,未获得授权的翻译作品的著作权仍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至于该翻译作品在行使其著作权时对原作著作权的侵犯,应由原作作者来向翻译者主张权利。
对于未经原作作者授权而翻译的作品的著作权是否有瑕疵,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提出在我国应适用三段划分法,这是较科学的。1991年6月1日,《著作权法》施行之前为第一时间段。彼时,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外国人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公民可以不经许可翻译外国作品而享有该翻译作品的著作权。本案即涉及此时间段。蔡兴文等四人对《马克思的自白》一书的翻译及出版,彭某对同一俄文作品的翻译及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均处于这一时间段。虽然蔡兴文等四人和彭某均未取得俄文原著作者的授权,但如果这两种译本之间不存在侵权关系的话,就均应享有翻译作品的完整的著作权。《著作权法》施行后至我国参加有关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前为第二时间段。我国《著作权法》并不是对所有外国作品都给予保护。该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而我国在1991年6月1日《著作权法》开始施行时尚未与他国签订过保护著作权的双边协议,也没有参加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直至1992年10月15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时《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三款才真正具有司法上的意义。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时间差的出现。虽说只有短短的16个半月的时间,但如果一位译者在这一时间段未经外国原作者授权而翻译的作品之著作权是没有瑕疵的。1992年10月15日之后的时间为第三时间段,凡与我国同为有关保护著作权国际公约的成员国或与我国有相关的双边协议的国家的公民的作品,均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2)对于针对同一部外文作品而产生的两部翻译作品之间是否存在著作权侵权应如何认定。对同一部外文作品有两个甚至三个以上不同的中文译本是很常见的,比如,朱生豪和梁实秋就都曾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如果两位译者对同一外文作品各自独立进行翻译,两种译本之间就不会存在侵权的情况。由于翻译作品是以原作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演绎作品,不同的译者针对同一原作进行翻译,两个译本在内容上应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不同译者的水平、翻译习惯、对原作的理解不同,在译文上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必然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在对彭译本和蔡译本进行鉴定时,鉴定人员独立翻译了部分《马克思自白》的原文,其译文与原、被告的译本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排除了译文是原作的“惟一表达形式”的可能,故独立创作的译文是具有独创性的,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对于不同译者的作品而言,翻译讲究“信、达、雅”,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在“信”这一层面上,针对同一外文作品的两部译作应该是区别不大的。而且《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是作品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能仅凭后译与前译在内容上的相同或近似就判断后译抄袭了前译,对前译构成著作权侵权。《著作权法》对作品外在形式的保护,具体到翻译作品而言,就是保护该作品的遣词造句,句法结构的形式等,即所谓“信、达、雅”中的“达”和“雅”的层面。译者的翻译水平,语言特色以及创造性劳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但判断后译作品对前译作品是否构成抄袭,不能仅凭某些词语句式上的相同或相似来认定。由于前译后译均来源于原作,很多词语和句式在上下文所限制的特定的语境中只能做一种解释,一种译法。具体到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值得注意。蔡译本与彭译本相比,在文字表达上共有162处相同或相似,可分为五类:
一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有30处;
二是部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由译者翻译15处;
三是短语2处;
四是完全由译者翻译共69处;
五是46条注释。
对于上述双方共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原文的部分,是不能认定为抄袭的。不同译者在对同一部西方作品进行翻译时,此问题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对原文中所引用《圣经》中的语言的翻译。虽然《圣经》的中译本版本很多,但如果两位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中所引述的《圣经》上的语言时,恰好参考的是相同的《圣经》中译本的话,就不能因为这部分译文的相同或相似而认定后译者对前译者进行了抄袭。在对后译作品是否抄袭了前译作品的判定中,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可能接触前译著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具体到我们正在探讨的个案,认定彭译本对蔡译本进行了部分抄袭,必须有彭某在翻译过程中接触过蔡译本的证据,但又不能仅凭接触而认定抄袭,彭某在翻译《马克思的自白》一书时有权阅读参考其他译本,包括蔡译本。在具备了有可能接触这一必要条件后,还要有其他证据在案佐证才可以认定抄袭事实的存在。在本案中彭某对其译本中排除了共同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部分外,仍有约23000字的内容与蔡译本文字表达相同或相似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再加上翻译过程中彭某接触过蔡译本的事实,就可以认定抄袭事实的存在。
起点商标作为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产交易信息请点击 【在线咨询】或添加微信 【19522093243】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此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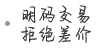
 商标分类
商标分类  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