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性使用与相关公众混淆之虞
 2021-02-06 10:02:58|
2021-02-06 10:02:58| 267|
267| 起点商标网
起点商标网 相比于“当作商标使用”的解释,把“商标性使用”解释为把他人注册为商标的标志“当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使用”,更合乎商标制度的宗旨。现代意义的商标本质上就是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商标保护是为了“确保所有带有同样商标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同一家对其质量负责的企业”*。商标法通说认为,注册商标权是一种排他权,赋予权利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相同或近似标志而易使相关公众混淆的行为*。由此,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当被告所使用的标志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且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才可能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应受到注册商标权控制。这似乎表明,商标性使用应该是侵犯注册商标权的先决条件。
然而,上述形式逻辑的推理无意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如何判断被告将注册为商标的标志“当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使用”?是依据被告的主观状态,还是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呢?遗憾的是,这两者都差强人意。对于主观状态来说,法律上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被告的主观状态不可不考虑。倘若被告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他人的注册商标当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借此混淆视听,其攀附商誉之心昭然,商标法理应给予否定性评价。为此,只要证明被告存在上述故意,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就认为应该认定被诉行为是“商标性使用”*。另一方面,又不可把被告主观状态作为决定性因素。如果被告把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志作为装饰图案使用到相同商品之上,不能仅因为被告的主观意图是美化商品而非识别商品来源而放纵他,不顾相关公众的实际认知状况。为此,尽管加拿大《商标法》第2条规定,“商标”是指为了或者实际把自己制造、销售、出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的区别开而采取的标志,但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判决却坚持认为,此处的“为了”(for the purpose of)不应当解释为“具有主观意愿”(with the intention),商标性使用不要求被告必须具有使用被诉标志以识别商品来源的主观故意*。
对于客观认知论来说,法理困难更为明显。被告常会主张被诉标志不是作为商标使用,而是作为企业字号、商品装潢等使用,并不识别商品来源;在其制售的商品之上另外显著地标有自己的商标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对此,法院难以直接得出结论说相关公众的确以被诉标志识别商品来源,原告不得不举证证明之。然而,原告举证被告如何使用争议标志已然无济于事。原告必须诉诸注册商标的显著性以及自己使用注册商标而积累的知名度,才可能证明被诉标志会被相关公众感知为“识别商品来源”*。例如,“辉瑞案”中,辉瑞公司生产销售的“万艾可”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药采用了蓝色菱形的注册商标,其知名度相当高。尽管蓝色菱形药片包装于不透明的材料里,消费者购买后服用之时,仍旧可以看到药片的形状和颜色。由此,并不能排除相关公众看到蓝色菱形抗男性功能障碍药可能误认为所购药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特定经济联系的经营主体。这种误认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原告已经不在证明被告的行为本身是否为商标性使用,而是证明被诉标志是否因为原告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而构成商标性使用。与其说这是在考察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商标性使用”,不如说是在考察相关公众混淆之虞本身——注册商标侵权行为的决定性条件。
面对被告主观状态说和相关公众客观认知说存在的法理困境,加拿大法院试图提出解决出路,但结果只能是徒劳。在2005年Tommy Hilfiger Licensing, Inc. v. International Clothiers Inc.案中,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只要证明被告主观状态或相关公众客观认知其中之一,即可满足“商标性使用”这一先决条件*。显然,这不能解决前述讨论到的法律问题。两者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都认为“商标性使用”的考察对象就是被诉标志本身,无须考虑原告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也就是说,商标性使用是一个绝对判断:无论被告是否知晓原告注册商标,亦不管相关公众是否对原告注册商标一无所知,只需证明被告意图使用被诉标志为商标,或者相关公众感知被诉标志为商标,就可以认定被告行为是否为“商标性使用”。
然而,问题在于,“商标性使用”是一种相对判断。相关公众之所以混淆,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知道原告的注册商标,而后异时异地见到被诉标志,误以为其为商品来源的标志。故商标性使用对于注册商标侵权而言,不应具有先决条件的法律地位;被告主观状态说和相关公众客观认知说所涉及的考虑因素都应该放到相关公众混淆之虞的判断过程中。为此,不奇怪,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美国少数以商标性使用为商标侵权先决条件的巡回上诉法院*——考察商标性使用就是判断被告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消费者混淆*。而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明确指出,商标性使用不是注册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商标性使用”即是“当作商标使用”(use as a trademark),主要考察被诉标志是否吸引公众注意力*。这相当于前述我国商标法下的“突出使用”,加拿大《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使受让人在转让时注意到商标和商品之间的联系”。至于被诉行为是否可能使相关公众混淆,美国法院采用多因素检验法,通盘考虑标志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全部相关因素*。无论是被告的主观状态,还是注册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被诉标志本身的使用形式都在考虑之列,均可用于评估相关公众混淆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在不同案件中,它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权重,而不必是决定性因素。为此,在美国传统商标法下,“商标性使用”代表一组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国制定法来看,并非所有的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都以相关公众混淆为条件。对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标志的“重同使用”(double identity)的情况,我国《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欧洲理事会协调成员国商标法一号指令》第5条第1款a项都明确规定是侵犯注册商标权,而未要求“容易导致混淆”。然而,这种立法方式过于僵硬,不值得提倡。通常情况下,“重同使用”容易导致混淆,但不尽然。例如,真车等比例模型玩具车,带有真车注册商标,相关公众也完全可能不认为模型玩具来自于该注册商标人,即便该注册商标同时也指定用于儿童玩具类商品*。法院最终仍应该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准绳,而不应直接认定为构成侵犯注册商标权。为此,TRIPS协议第16条第1款仅规定,“重同使用”应当推定(shall be presumed)为容易导致混淆。这种推定理应可以根据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诚然,上述制定法的缺陷可以通过引入“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来予以解决。但是,这样做会妨碍“重同使用”以外的商标侵权判断,包括同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标志,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可谓得不偿失。欧盟法院明确拒绝以“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为周全之计,欧盟法院又用心良苦地引入“损害注册商标基本功能”作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构成要件。在2002年Arsenal案中,原告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是英超联赛的著名足球俱乐部,“Arsenal”以及“Arsenal Gunner及图形”是其注册商标。被告未经许可,在其出售的围巾上使用了上述标志。但是,被告在足球赛场的看台上销售时,使用醒目大字标牌说明自己销售的围巾不是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正式许可的产品,相关文字和标志使用仅为美化商品,用以表示衷心支持阿森纳足球队。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认为被告的使用行为不是商标性使用,不侵犯注册商标权。但是,欧盟法院认为,识别商品来源是商标的基本功能,任何行为只要损害这一基本功能,都可能侵犯注册商标权。被诉行为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志,会造成原被告商品存在实质性联系的错误印象,可损害注册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尽管被告在销售点立有免责声明,但销售点之外的公众看到其售出的围巾,仍可误认为来自于注册商标权人*。可见,欧盟法院认为,不应割裂考察被告行为是否为“商标性使用”,并以此作为判定注册商标侵权判定的先决条件。在Arsenal案之后,欧盟法院即以损害商标基本功能为各种注册商标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尤其强调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6]1243。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两者都反对以“商标性使用”作为先决条件,并且都强调判断侵犯注册商标权时,应当考察被诉标志使用“行为”整体,包括具体商业使用情景的全部相关因素。究其根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以不构成商标性使用为由,认定侵犯注册商标权不成立,可能错误地放纵混淆相关公众,因为这种做法孤立地考察被诉标志;第二,片面地强调“商标性使用”可能不合理地把商标侵权判断局限于隔离比对被诉标志本身与注册商标,而不是考察被诉标识行为整体所产生的商业影响,由此不适当地限制注册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那么,《商标法》(2013)在2014年5月1日生效之后,我国应该何去何从?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和欧盟的做法并无实质性差别。从法条规定来看,我国《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第2项与《欧洲理事会协调成员国商标法一号指令》第5条第1款a项和b项也无实质性差别。如果坚持以“商标性使用”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即便效仿加拿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前述做法,也无法克服“商标性使用”对注册商标权的不适当限制。相比之下,符合法理而又适宜的做法是效仿欧盟法院,放弃“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先决条件的法律观点,转而强调被诉行为损害商标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我国不少判例已经从商标基本功能的角度推理论证商标侵权*。为此,法院需要阐明的主要是,《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第2项所谓“使用……商标”的含义不同于第48条定义的“商标的使用”。
然而,上述形式逻辑的推理无意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如何判断被告将注册为商标的标志“当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使用”?是依据被告的主观状态,还是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呢?遗憾的是,这两者都差强人意。对于主观状态来说,法律上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被告的主观状态不可不考虑。倘若被告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他人的注册商标当作识别商品来源的标志,借此混淆视听,其攀附商誉之心昭然,商标法理应给予否定性评价。为此,只要证明被告存在上述故意,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就认为应该认定被诉行为是“商标性使用”*。另一方面,又不可把被告主观状态作为决定性因素。如果被告把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志作为装饰图案使用到相同商品之上,不能仅因为被告的主观意图是美化商品而非识别商品来源而放纵他,不顾相关公众的实际认知状况。为此,尽管加拿大《商标法》第2条规定,“商标”是指为了或者实际把自己制造、销售、出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的区别开而采取的标志,但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判决却坚持认为,此处的“为了”(for the purpose of)不应当解释为“具有主观意愿”(with the intention),商标性使用不要求被告必须具有使用被诉标志以识别商品来源的主观故意*。
对于客观认知论来说,法理困难更为明显。被告常会主张被诉标志不是作为商标使用,而是作为企业字号、商品装潢等使用,并不识别商品来源;在其制售的商品之上另外显著地标有自己的商标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对此,法院难以直接得出结论说相关公众的确以被诉标志识别商品来源,原告不得不举证证明之。然而,原告举证被告如何使用争议标志已然无济于事。原告必须诉诸注册商标的显著性以及自己使用注册商标而积累的知名度,才可能证明被诉标志会被相关公众感知为“识别商品来源”*。例如,“辉瑞案”中,辉瑞公司生产销售的“万艾可”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药采用了蓝色菱形的注册商标,其知名度相当高。尽管蓝色菱形药片包装于不透明的材料里,消费者购买后服用之时,仍旧可以看到药片的形状和颜色。由此,并不能排除相关公众看到蓝色菱形抗男性功能障碍药可能误认为所购药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特定经济联系的经营主体。这种误认可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原告已经不在证明被告的行为本身是否为商标性使用,而是证明被诉标志是否因为原告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而构成商标性使用。与其说这是在考察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商标性使用”,不如说是在考察相关公众混淆之虞本身——注册商标侵权行为的决定性条件。
面对被告主观状态说和相关公众客观认知说存在的法理困境,加拿大法院试图提出解决出路,但结果只能是徒劳。在2005年Tommy Hilfiger Licensing, Inc. v. International Clothiers Inc.案中,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只要证明被告主观状态或相关公众客观认知其中之一,即可满足“商标性使用”这一先决条件*。显然,这不能解决前述讨论到的法律问题。两者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都认为“商标性使用”的考察对象就是被诉标志本身,无须考虑原告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也就是说,商标性使用是一个绝对判断:无论被告是否知晓原告注册商标,亦不管相关公众是否对原告注册商标一无所知,只需证明被告意图使用被诉标志为商标,或者相关公众感知被诉标志为商标,就可以认定被告行为是否为“商标性使用”。
然而,问题在于,“商标性使用”是一种相对判断。相关公众之所以混淆,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知道原告的注册商标,而后异时异地见到被诉标志,误以为其为商品来源的标志。故商标性使用对于注册商标侵权而言,不应具有先决条件的法律地位;被告主观状态说和相关公众客观认知说所涉及的考虑因素都应该放到相关公众混淆之虞的判断过程中。为此,不奇怪,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美国少数以商标性使用为商标侵权先决条件的巡回上诉法院*——考察商标性使用就是判断被告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消费者混淆*。而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则明确指出,商标性使用不是注册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商标性使用”即是“当作商标使用”(use as a trademark),主要考察被诉标志是否吸引公众注意力*。这相当于前述我国商标法下的“突出使用”,加拿大《商标法》第四条规定的“使受让人在转让时注意到商标和商品之间的联系”。至于被诉行为是否可能使相关公众混淆,美国法院采用多因素检验法,通盘考虑标志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全部相关因素*。无论是被告的主观状态,还是注册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被诉标志本身的使用形式都在考虑之列,均可用于评估相关公众混淆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在不同案件中,它们可以具有不同的权重,而不必是决定性因素。为此,在美国传统商标法下,“商标性使用”代表一组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国制定法来看,并非所有的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都以相关公众混淆为条件。对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标志的“重同使用”(double identity)的情况,我国《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欧洲理事会协调成员国商标法一号指令》第5条第1款a项都明确规定是侵犯注册商标权,而未要求“容易导致混淆”。然而,这种立法方式过于僵硬,不值得提倡。通常情况下,“重同使用”容易导致混淆,但不尽然。例如,真车等比例模型玩具车,带有真车注册商标,相关公众也完全可能不认为模型玩具来自于该注册商标人,即便该注册商标同时也指定用于儿童玩具类商品*。法院最终仍应该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准绳,而不应直接认定为构成侵犯注册商标权。为此,TRIPS协议第16条第1款仅规定,“重同使用”应当推定(shall be presumed)为容易导致混淆。这种推定理应可以根据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诚然,上述制定法的缺陷可以通过引入“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来予以解决。但是,这样做会妨碍“重同使用”以外的商标侵权判断,包括同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近似的标志,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可谓得不偿失。欧盟法院明确拒绝以“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为周全之计,欧盟法院又用心良苦地引入“损害注册商标基本功能”作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构成要件。在2002年Arsenal案中,原告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是英超联赛的著名足球俱乐部,“Arsenal”以及“Arsenal Gunner及图形”是其注册商标。被告未经许可,在其出售的围巾上使用了上述标志。但是,被告在足球赛场的看台上销售时,使用醒目大字标牌说明自己销售的围巾不是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正式许可的产品,相关文字和标志使用仅为美化商品,用以表示衷心支持阿森纳足球队。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认为被告的使用行为不是商标性使用,不侵犯注册商标权。但是,欧盟法院认为,识别商品来源是商标的基本功能,任何行为只要损害这一基本功能,都可能侵犯注册商标权。被诉行为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标志,会造成原被告商品存在实质性联系的错误印象,可损害注册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尽管被告在销售点立有免责声明,但销售点之外的公众看到其售出的围巾,仍可误认为来自于注册商标权人*。可见,欧盟法院认为,不应割裂考察被告行为是否为“商标性使用”,并以此作为判定注册商标侵权判定的先决条件。在Arsenal案之后,欧盟法院即以损害商标基本功能为各种注册商标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尤其强调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6]1243。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两者都反对以“商标性使用”作为先决条件,并且都强调判断侵犯注册商标权时,应当考察被诉标志使用“行为”整体,包括具体商业使用情景的全部相关因素。究其根本,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以不构成商标性使用为由,认定侵犯注册商标权不成立,可能错误地放纵混淆相关公众,因为这种做法孤立地考察被诉标志;第二,片面地强调“商标性使用”可能不合理地把商标侵权判断局限于隔离比对被诉标志本身与注册商标,而不是考察被诉标识行为整体所产生的商业影响,由此不适当地限制注册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那么,《商标法》(2013)在2014年5月1日生效之后,我国应该何去何从?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和欧盟的做法并无实质性差别。从法条规定来看,我国《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第2项与《欧洲理事会协调成员国商标法一号指令》第5条第1款a项和b项也无实质性差别。如果坚持以“商标性使用”为注册商标侵权的先决条件,即便效仿加拿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前述做法,也无法克服“商标性使用”对注册商标权的不适当限制。相比之下,符合法理而又适宜的做法是效仿欧盟法院,放弃“商标性使用”作为注册商标侵权先决条件的法律观点,转而强调被诉行为损害商标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我国不少判例已经从商标基本功能的角度推理论证商标侵权*。为此,法院需要阐明的主要是,《商标法》(2013)第57条第1项和第2项所谓“使用……商标”的含义不同于第48条定义的“商标的使用”。
起点商标作为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产交易信息请点击 【在线咨询】或添加微信 【19522093243】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此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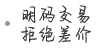
 商标分类
商标分类  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