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注册破除地名的“神圣性”
 2021-02-06 10:02:29|
2021-02-06 10:02:29| 286|
286| 起点商标网
起点商标网 实际上,已有学者探究了立法者的真实初衷,只可惜未展开充分论述,如邓宏光教授指出:“我国这种地名商标的规定,与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伦理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当时企业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国营企业,商标注册意识淡薄,而等级观念却很强。主管部门可能认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是由政府界定的,将这些地名用作商标使用,无形之中就在商业上利用了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当然应当禁止,而使用民间流传的地名则不存在这种结果。”(19)可见,立法者是把某些地名作为政治符号看待而神圣化了。按照语言学和传播学的观点,所谓“政治符号”,即“一种使用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等。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20)政治符号是意义表述、价值展现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通常构成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政治“主观领域”中承担着提供社会记忆、寻求政治认同、整合意识形态、实施社会秩序再生产等重要政治功能。(21)恰如有研究者所言:“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22)可见,特定地名不仅仅指代某一地理空间,更承载强烈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具有公共色彩。我国无论是《宪法》还是《商标法》,都体现了对“国家级别”政治符号的特别保护,如《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明确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国歌、军旗、军徽、军歌、勋章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的名称、标志、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地理位置(大到江河湖海,小到街巷楼门)的命名、更名及撤名都受到行政机关的严格管理,乃至于在2019年6月,海南、广东、河北等省份着手清理“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引发了广泛热议。
布迪厄认为:“符号和符号体系作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它是被塑造结构的,也有塑造结构的权力。”(23)这里,“被塑造结构”和“塑造结构”是符号权力的两个向度,前者体现为生产和再生产符号与符号体系的权力,后者则体现为符号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知识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向度,因为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向度。”(24)受此思潮影响,20世纪80年代地名学也开始将视角转向文化、经济和政治研究,探讨空间如何作为知识符号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文化意义如何促进特定社会实践,并构建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而不再仅将地名视为特定地理空间的指代物。恰如有研究者所言:“地名作为城市记忆中符号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符号要素象征性、交流互动性和叙事性的功能,在城市中成为沟通城市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特定符号。地名能够反映城市与社会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发展状况,往往代表着城市的身份特征,与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社会关系、个人情感紧密相连。”(25)但并非所有地名都具有文化内涵或政治寓意。不仅如此,不同地名符号与文化政治隐喻之间的对应关系强弱程度不一,并且常常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不定。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地名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地方空间和资源的争夺,地名的赋予与改变代表着领域分割及权力的更迭,是空间边界与实体的争夺与协商”。(26)在多方利益主体的漫长博弈之中,地名也便在方位指示功能与治理教化功能之间来回摇摆。(27)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法律体系本身找到这一论点的依据。实际上,立法者并没有把地名同前述“国家级别”的政治符号等同视之,而是在第10条第1款之外,单立了一款,并规定具有“其他含义”或属于地理标志或已经注册的地名仍可作为商标使用。这种“杂糅”的立法例非常特别,它既不同于其他国家关于地名商标可注册性的规定及理由,又造成自身逻辑的混乱与复杂,导致法律适用的矛盾对立与高度不确定性,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而修改的首要前提就是破除地名的“神圣性”。就符号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理论学说,首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由“有声形象”构成,“所指”则是该有声形象在我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28)符号都是功能性存在,其之所以有含义(即特定能指与特定所指产生关联),是因为符号指代了外在于自身的其他事物。索绪尔及之后的符号学家进一步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固有联系,其关联是自由的、任意的,或者说约定俗成的,即任何符号的含义都是以集体习惯为基础的,一旦语言社团确定了一个符号,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它。(29)
这充分说明,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比利时画家马格里特有幅杰作就表达了这层哲理,画面上是一只大大的烟斗,烟斗下面写了“这不是烟斗”几个字。法国哲学家福柯还专门就此写了篇短文《这不是烟斗》,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30)根据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符号的生成和理解都是认知主体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其含义既不能在世界中,也不能在语言符号系统内部去寻找。含义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要理解一个语言符号的含义,必须依靠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他认知结构(即语境)。(31)由此可见,词语的含义是可以变化的,作为“词”的地名,其在特定语境下指代某个地理位置并衍生出某种政治寓意,但如果换一个语境,则完全可以产生其他含义,如“华盛顿”可以是地名乃至政治意味上的国家首都,也可以是人名——具体什么含义,完全取决于认知主体所处的语境,没有谁一定强于谁的固定准则。同样地,地名也可以用于指代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即扮演商标的角色。当然,由于地名本身具备固有含义,相关公众很难马上摆脱这一固有含义而直接将其认知理解为一个商标,但经过长期持续的使用和宣传,作为符号的地名完全可以产生商标意义上的显著性(即“第二含义”)。这种显著性意味着经营者建立了相当的市场声誉,实现了相关公众认“牌”购物,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确认和保护这种显著性和商誉,显然符合商标法的立法初衷和宗旨,这也正是为何大多数国家均规定地名经使用获得显著性后,可以注册为商标的根本原因。(32)当然,在商业语境下地名的第一层含义并没有彻底消失,消费者仍然可能会联想到某符号还有地名上的含义乃至某种政治寓意,但也就到此为止,而不至于煞有介事地认为这会产生诸如侮辱、贬损等不良后果。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地名可以去神圣化,那所有政治符号都可以作为商标使用并加以注册。笔者认为,这样的推理是不成立的。因为首先,绝大多数地名并非政治符号,哪怕其行政区划级别较高或广为公众知晓,除非是具有极强政治象征意义的地名,如天安门;其次,地名经长期使用获得显著性从而满足商标注册的条件,并不意味政治符号也可以产生“第二含义”。虽然符号能指与所指之连接是任意的,或者说词与物之间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但早有学者指出,语言符号中约70%的表达方式与隐喻有关。隐喻被看作是概念结构中认知图式的转移,是人类一种普遍的认知现象。因此,人类概念系统大多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广泛存在的隐喻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任意性”学说的一种修正,它说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有思维纽带的。(33)政治符号就是一种强隐喻,如中国人一看到五星红旗、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隐喻越强,词与物之间的既有对应关系不仅越难被打破,反而通过宣扬和传播更加巩固;最后,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秩序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任何国家在其商标化问题上都会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或明确加以禁止,但地名的不可商标性却并不具有这种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基础,加上有其他规则(如除非经使用产生了显著性,具有描述性的产地名称不得注册为商标;地名商标不能带有欺骗性;允许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以及地名商标的正当使用等)的联合约束,那种认为一旦肯定地名的可商标性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的顾虑是不必要的。更何况,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 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如此众多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中,其中绝大多数并不存在政治象征意义;相反,一些具有一定政治寓意的地名(如中南海、钓鱼岛、宝塔山)却可能因为其不属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而不能阻止其被注册为商标(至少不能依据《商标法》第10条第2款加以阻止),这就造成一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对此我们应当通盘考虑整个商标法的制度体系。
布迪厄认为:“符号和符号体系作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它是被塑造结构的,也有塑造结构的权力。”(23)这里,“被塑造结构”和“塑造结构”是符号权力的两个向度,前者体现为生产和再生产符号与符号体系的权力,后者则体现为符号在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知识理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向度,因为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向度。”(24)受此思潮影响,20世纪80年代地名学也开始将视角转向文化、经济和政治研究,探讨空间如何作为知识符号来表达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文化意义如何促进特定社会实践,并构建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而不再仅将地名视为特定地理空间的指代物。恰如有研究者所言:“地名作为城市记忆中符号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符号要素象征性、交流互动性和叙事性的功能,在城市中成为沟通城市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特定符号。地名能够反映城市与社会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发展状况,往往代表着城市的身份特征,与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社会关系、个人情感紧密相连。”(25)但并非所有地名都具有文化内涵或政治寓意。不仅如此,不同地名符号与文化政治隐喻之间的对应关系强弱程度不一,并且常常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不定。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地名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地方空间和资源的争夺,地名的赋予与改变代表着领域分割及权力的更迭,是空间边界与实体的争夺与协商”。(26)在多方利益主体的漫长博弈之中,地名也便在方位指示功能与治理教化功能之间来回摇摆。(27)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法律体系本身找到这一论点的依据。实际上,立法者并没有把地名同前述“国家级别”的政治符号等同视之,而是在第10条第1款之外,单立了一款,并规定具有“其他含义”或属于地理标志或已经注册的地名仍可作为商标使用。这种“杂糅”的立法例非常特别,它既不同于其他国家关于地名商标可注册性的规定及理由,又造成自身逻辑的混乱与复杂,导致法律适用的矛盾对立与高度不确定性,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而修改的首要前提就是破除地名的“神圣性”。就符号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理论学说,首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由“有声形象”构成,“所指”则是该有声形象在我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28)符号都是功能性存在,其之所以有含义(即特定能指与特定所指产生关联),是因为符号指代了外在于自身的其他事物。索绪尔及之后的符号学家进一步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固有联系,其关联是自由的、任意的,或者说约定俗成的,即任何符号的含义都是以集体习惯为基础的,一旦语言社团确定了一个符号,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它。(29)
这充分说明,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固定不变。比利时画家马格里特有幅杰作就表达了这层哲理,画面上是一只大大的烟斗,烟斗下面写了“这不是烟斗”几个字。法国哲学家福柯还专门就此写了篇短文《这不是烟斗》,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30)根据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符号的生成和理解都是认知主体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其含义既不能在世界中,也不能在语言符号系统内部去寻找。含义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要理解一个语言符号的含义,必须依靠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他认知结构(即语境)。(31)由此可见,词语的含义是可以变化的,作为“词”的地名,其在特定语境下指代某个地理位置并衍生出某种政治寓意,但如果换一个语境,则完全可以产生其他含义,如“华盛顿”可以是地名乃至政治意味上的国家首都,也可以是人名——具体什么含义,完全取决于认知主体所处的语境,没有谁一定强于谁的固定准则。同样地,地名也可以用于指代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即扮演商标的角色。当然,由于地名本身具备固有含义,相关公众很难马上摆脱这一固有含义而直接将其认知理解为一个商标,但经过长期持续的使用和宣传,作为符号的地名完全可以产生商标意义上的显著性(即“第二含义”)。这种显著性意味着经营者建立了相当的市场声誉,实现了相关公众认“牌”购物,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确认和保护这种显著性和商誉,显然符合商标法的立法初衷和宗旨,这也正是为何大多数国家均规定地名经使用获得显著性后,可以注册为商标的根本原因。(32)当然,在商业语境下地名的第一层含义并没有彻底消失,消费者仍然可能会联想到某符号还有地名上的含义乃至某种政治寓意,但也就到此为止,而不至于煞有介事地认为这会产生诸如侮辱、贬损等不良后果。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地名可以去神圣化,那所有政治符号都可以作为商标使用并加以注册。笔者认为,这样的推理是不成立的。因为首先,绝大多数地名并非政治符号,哪怕其行政区划级别较高或广为公众知晓,除非是具有极强政治象征意义的地名,如天安门;其次,地名经长期使用获得显著性从而满足商标注册的条件,并不意味政治符号也可以产生“第二含义”。虽然符号能指与所指之连接是任意的,或者说词与物之间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但早有学者指出,语言符号中约70%的表达方式与隐喻有关。隐喻被看作是概念结构中认知图式的转移,是人类一种普遍的认知现象。因此,人类概念系统大多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广泛存在的隐喻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任意性”学说的一种修正,它说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有思维纽带的。(33)政治符号就是一种强隐喻,如中国人一看到五星红旗、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隐喻越强,词与物之间的既有对应关系不仅越难被打破,反而通过宣扬和传播更加巩固;最后,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秩序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任何国家在其商标化问题上都会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或明确加以禁止,但地名的不可商标性却并不具有这种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基础,加上有其他规则(如除非经使用产生了显著性,具有描述性的产地名称不得注册为商标;地名商标不能带有欺骗性;允许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以及地名商标的正当使用等)的联合约束,那种认为一旦肯定地名的可商标性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的顾虑是不必要的。更何况,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 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在如此众多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中,其中绝大多数并不存在政治象征意义;相反,一些具有一定政治寓意的地名(如中南海、钓鱼岛、宝塔山)却可能因为其不属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而不能阻止其被注册为商标(至少不能依据《商标法》第10条第2款加以阻止),这就造成一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对此我们应当通盘考虑整个商标法的制度体系。
起点商标作为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产交易信息请点击 【在线咨询】或添加微信 【19522093243】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此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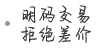
 商标分类
商标分类  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