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机关对定牌加工侵权的态度演变及主要理论依据
 2021-02-01 13:02:48|
2021-02-01 13:02:48| 265|
265| 起点商标网
起点商标网 (一)“亲商标权人”时期
我国早期司法判决较多强调商标权的地域性,认定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的贴牌行为并不属于法外情况,其行为属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商标使用”,只要产生混淆的,就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如果国内注册商标与贴牌标识相同,商品类别一样,我国法院一般都推断存在混淆,径直认定构成侵权。例如2001年耐克公司诉银兴制衣(NIKE)案、②2005年瑞宝公司诉余姚工商局(RBI)案和2006年泓信公司诉广州海关(HENKEL)案。③但是,如果法院认定两个标识或两种产品并不近似,或者虽然相似但依旧不构成混淆的,则不构成侵权。例如2005年聚宝公司诉义务市工商局(Rize)案、④雨果博斯诉喜乐制衣(Boss)案,⑤法院认定不存在混淆,因此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在这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也频繁撰文,以商标权地域性为基础,支持认定OEM受托方加工相同产品、贴附相同商标并交付至境外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⑥然而,在这段时期也有个别法院和法官认为OEM实际类似于加工车间,并不导致市场混淆,也没有损失产生,因此不宜认为构成侵权。⑦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直接提出OEM不应当认定构成侵权,⑧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形成主流的司法意见。
(二)“亲OEM受托方”时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法院审结的涉外定牌加工案件逐渐增加。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和中国裁判文书网,对2007~2018年之间每年审结的有公开裁判文书的OEM案件数量进行梳理,共检索得到将近100个OEM商标侵权案件,其中2014年前后我国OEM商标侵权案件审结量达到高峰(表1)。
与此同时,司法的风向标也逐渐出现了变化。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政策文件中尚提出,应该结合OEM受托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商标侵权责任的承担。①但到了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回复海关总署的《关于对<贴牌加工出口产品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的复函》中却指出,在OEM情况下,由于涉案相关标识在我国境内不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不会产生混淆误认,OEM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②在《商标法》修订前后,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孔祥俊也明确提出,贴附委托人商标的涉外贴牌不发挥《商标法》规定的识别功能,也未造成损害,不构成商标侵权。③由此,我国法院逐渐确立OEM属于非商标使用、不可能产生混淆的观点。
司法系统用以支持OEM加工企业的观点和理论还进一步影响到了我国2013年《商标法》的第三次修订。新《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在定义“商标的使用”时,在原《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基础上加入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的表述。另外,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在规定“商标侵权行为”时,将原《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1项拆分为两条,并在相似侵权情形中明确加入了“容易引起混淆的”这一要件。④上述修改也为司法机关在OEM案件中适用“商标性使用”概念和“混淆可能性”判断提供了立法上的基础。
在上述趋势之下,我国法院审理OEM商标侵权案件的思路也固定如下:(1)通常先认定是否属于OEM,然后再分析是否具备商标使用的性质;(2)如果不属于OEM,则进行正常的混淆判断,再判定OEM受托方是否构成商标侵权;(3)如果属于OEM,通常判定OEM受托方贴附商标并交付到境外的行为并非是《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商标使用”,可以直接判定不侵权;或者(4)基于境外销售和相关公众不在境内的事实,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认定不存在境内的“混淆可能性”从而不构成商标侵权。
对应上述司法态度的转变和法律适用的空间,近年我国法院针对OEM受托方贴牌行为判定不侵权的比重在快速增加。同样以上述统计的过去10年的案件裁判文书为例,其中认定OEM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的占到60%甚至80%以上(表2)。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决中认定商标侵权与否的理由,可以发现:第一,在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案件中,有50%以上的案件,法院认为涉外定牌受托方的加工、贴牌和交付行为属于“非商标使用”,而有近50%的案件,法院认为“无混淆可能性”;第二,在认定商标侵权的判决中,有超过50%的案件,法院认为是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不能证明存在OEM关系。可以合理推断,支持OEM不侵权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在这些认定商标侵权的案件中,一旦OEM受托方能够证明OEM关系的存在,那么在“非商标使用”或“无混淆可能性”理论之下,判决结果极有可能会被改写(表2)。
表2 我国法院OEM受托方商标侵权判决结果及理由(2007~2018年)
(三)OEM非商标使用的大一统时期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审PRETUL案,在推翻下级法院有关OEM委托方行为构成商标使用的判决时指出,该案虽然仍适用2001年《商标法》,但应当考虑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已经对商标使用概念做出了澄清,据此应避免将不属于商标使用的行为归入这一范畴,进而导致《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扩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指出,OEM受托方贴附的标识在我国境内仅发挥物理作用,为委托方在国外使用商标提供了必要性技术条件,在我国境内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故该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在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商标不发生识别作用的情况下,判断是否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或者判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造成混淆,都不具有实际意义。①
在该指导性案例出台之后,法院基本都认定OEM不具有商标使用的性质,而仅是物理意义的技术添附。但是,即便在该案之后,在与OEM相关的商标撤销行政诉讼中,仍有法院认为委托加工、贴牌并出口的行为属于积极使用商标的行为。①譬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曾坚持认定OEM行为属于“撤三”案件中的“商标使用”,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号判决系针对定牌加工是否属于修改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情形,不能成为判定是否属于‘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当然依据’”。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认为,国内商标权人通过授权许可他人委托定牌加工生产并出口,属于积极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尽管不在国内销售,也不会因废置商标而撤销。③这种同样行为在不同案件类型中有不同性质认定的局面直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15日认定OEM行为同样不属于“撤三”商标行政案件中的“商标使用”才基本得到缓解。④
(四)夹缝中的折中之道:对OEM受托方必要审查注意义务的关注
在前述侵权与不侵权的两个极端之间,还出现了另外一类判决,要求结合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的过错(特别是其是否履行了必要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这种观点最初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之中。⑤OEM形态的多元化,特别是反向OEM等损害国内民族品牌利益行为的出现,也为该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功利性诉求。在2014年上柴公司诉常佳(东风)公司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贴附商标的行为不识别商品来源,不属于商标使用,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涉案“东风”商标为驰名商标,受托方未尽合理注意与避让义务为由,判定构成商标侵权。⑥虽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侵权结论最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判决所否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完全否定OEM受托方的必要审查注意义务,而是指出“除非有相反证据显示常佳公司接受委托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上柴公司的商标权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侵害商标权。本案中,常佳公司已经审查了相关权利证书资料,充分关注了委托方的商标权利状态。在印度尼西亚相关司法机构判决相关商标归属上柴公司期间,还就当时的定牌加工行为与上柴公司沟通并签订协议,支付了补偿费用。可见,常佳公司对于相关商标权利状况已经适当履行了审慎适当的注意义务。”在2019年之前,坚持上述观点的OEM案件还有2016年于逊刚诉浙江容大(Roadage)案⑦以及匹克诉振宇、美国伊萨克莫里斯(Peak)案⑧等。由此看来,根据OEM受托方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来认定侵权与否,似乎可以成为司法机关在特定OEM案件里对“非商标性使用”理论施以一定限制的主要依据。这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司法机关在面对商标权人利益和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一种折中路径。
(五)转变并回归“商标使用”的本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9月23日判决的HONDA案中,终于改变了自己十来年的立场,判决两被告的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应当依据《商标法》做出整体一致的解释。如果当事人在生产制造或加工的产品上“以标注方式或其他方式使用了商标”,只要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就应当认定该使用状态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商品没有投入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没有实际接触该商品,就否认存在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而且,《商标法》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并不要求确实发生了混淆,而仅指如果接触到有可能发生混淆。
我国早期司法判决较多强调商标权的地域性,认定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的贴牌行为并不属于法外情况,其行为属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商标使用”,只要产生混淆的,就应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如果国内注册商标与贴牌标识相同,商品类别一样,我国法院一般都推断存在混淆,径直认定构成侵权。例如2001年耐克公司诉银兴制衣(NIKE)案、②2005年瑞宝公司诉余姚工商局(RBI)案和2006年泓信公司诉广州海关(HENKEL)案。③但是,如果法院认定两个标识或两种产品并不近似,或者虽然相似但依旧不构成混淆的,则不构成侵权。例如2005年聚宝公司诉义务市工商局(Rize)案、④雨果博斯诉喜乐制衣(Boss)案,⑤法院认定不存在混淆,因此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在这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也频繁撰文,以商标权地域性为基础,支持认定OEM受托方加工相同产品、贴附相同商标并交付至境外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⑥然而,在这段时期也有个别法院和法官认为OEM实际类似于加工车间,并不导致市场混淆,也没有损失产生,因此不宜认为构成侵权。⑦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直接提出OEM不应当认定构成侵权,⑧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形成主流的司法意见。
(二)“亲OEM受托方”时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法院审结的涉外定牌加工案件逐渐增加。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和中国裁判文书网,对2007~2018年之间每年审结的有公开裁判文书的OEM案件数量进行梳理,共检索得到将近100个OEM商标侵权案件,其中2014年前后我国OEM商标侵权案件审结量达到高峰(表1)。
与此同时,司法的风向标也逐渐出现了变化。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政策文件中尚提出,应该结合OEM受托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商标侵权责任的承担。①但到了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回复海关总署的《关于对<贴牌加工出口产品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的复函》中却指出,在OEM情况下,由于涉案相关标识在我国境内不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不会产生混淆误认,OEM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②在《商标法》修订前后,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孔祥俊也明确提出,贴附委托人商标的涉外贴牌不发挥《商标法》规定的识别功能,也未造成损害,不构成商标侵权。③由此,我国法院逐渐确立OEM属于非商标使用、不可能产生混淆的观点。
司法系统用以支持OEM加工企业的观点和理论还进一步影响到了我国2013年《商标法》的第三次修订。新《商标法》第四十八条在定义“商标的使用”时,在原《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基础上加入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的表述。另外,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在规定“商标侵权行为”时,将原《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1项拆分为两条,并在相似侵权情形中明确加入了“容易引起混淆的”这一要件。④上述修改也为司法机关在OEM案件中适用“商标性使用”概念和“混淆可能性”判断提供了立法上的基础。
在上述趋势之下,我国法院审理OEM商标侵权案件的思路也固定如下:(1)通常先认定是否属于OEM,然后再分析是否具备商标使用的性质;(2)如果不属于OEM,则进行正常的混淆判断,再判定OEM受托方是否构成商标侵权;(3)如果属于OEM,通常判定OEM受托方贴附商标并交付到境外的行为并非是《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商标使用”,可以直接判定不侵权;或者(4)基于境外销售和相关公众不在境内的事实,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认定不存在境内的“混淆可能性”从而不构成商标侵权。
对应上述司法态度的转变和法律适用的空间,近年我国法院针对OEM受托方贴牌行为判定不侵权的比重在快速增加。同样以上述统计的过去10年的案件裁判文书为例,其中认定OEM受托方不构成商标侵权的占到60%甚至80%以上(表2)。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决中认定商标侵权与否的理由,可以发现:第一,在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案件中,有50%以上的案件,法院认为涉外定牌受托方的加工、贴牌和交付行为属于“非商标使用”,而有近50%的案件,法院认为“无混淆可能性”;第二,在认定商标侵权的判决中,有超过50%的案件,法院认为是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不能证明存在OEM关系。可以合理推断,支持OEM不侵权的比例应该更高,因为在这些认定商标侵权的案件中,一旦OEM受托方能够证明OEM关系的存在,那么在“非商标使用”或“无混淆可能性”理论之下,判决结果极有可能会被改写(表2)。
表2 我国法院OEM受托方商标侵权判决结果及理由(2007~2018年)
(三)OEM非商标使用的大一统时期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审PRETUL案,在推翻下级法院有关OEM委托方行为构成商标使用的判决时指出,该案虽然仍适用2001年《商标法》,但应当考虑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已经对商标使用概念做出了澄清,据此应避免将不属于商标使用的行为归入这一范畴,进而导致《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的扩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指出,OEM受托方贴附的标识在我国境内仅发挥物理作用,为委托方在国外使用商标提供了必要性技术条件,在我国境内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故该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在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商标不发生识别作用的情况下,判断是否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或者判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造成混淆,都不具有实际意义。①
在该指导性案例出台之后,法院基本都认定OEM不具有商标使用的性质,而仅是物理意义的技术添附。但是,即便在该案之后,在与OEM相关的商标撤销行政诉讼中,仍有法院认为委托加工、贴牌并出口的行为属于积极使用商标的行为。①譬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曾坚持认定OEM行为属于“撤三”案件中的“商标使用”,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号判决系针对定牌加工是否属于修改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情形,不能成为判定是否属于‘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的当然依据’”。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认为,国内商标权人通过授权许可他人委托定牌加工生产并出口,属于积极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尽管不在国内销售,也不会因废置商标而撤销。③这种同样行为在不同案件类型中有不同性质认定的局面直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15日认定OEM行为同样不属于“撤三”商标行政案件中的“商标使用”才基本得到缓解。④
(四)夹缝中的折中之道:对OEM受托方必要审查注意义务的关注
在前述侵权与不侵权的两个极端之间,还出现了另外一类判决,要求结合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的过错(特别是其是否履行了必要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这种观点最初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之中。⑤OEM形态的多元化,特别是反向OEM等损害国内民族品牌利益行为的出现,也为该理论提供了现实的功利性诉求。在2014年上柴公司诉常佳(东风)公司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贴附商标的行为不识别商品来源,不属于商标使用,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涉案“东风”商标为驰名商标,受托方未尽合理注意与避让义务为由,判定构成商标侵权。⑥虽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侵权结论最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判决所否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完全否定OEM受托方的必要审查注意义务,而是指出“除非有相反证据显示常佳公司接受委托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对上柴公司的商标权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侵害商标权。本案中,常佳公司已经审查了相关权利证书资料,充分关注了委托方的商标权利状态。在印度尼西亚相关司法机构判决相关商标归属上柴公司期间,还就当时的定牌加工行为与上柴公司沟通并签订协议,支付了补偿费用。可见,常佳公司对于相关商标权利状况已经适当履行了审慎适当的注意义务。”在2019年之前,坚持上述观点的OEM案件还有2016年于逊刚诉浙江容大(Roadage)案⑦以及匹克诉振宇、美国伊萨克莫里斯(Peak)案⑧等。由此看来,根据OEM受托方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来认定侵权与否,似乎可以成为司法机关在特定OEM案件里对“非商标性使用”理论施以一定限制的主要依据。这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司法机关在面对商标权人利益和涉外定牌加工受托方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一种折中路径。
(五)转变并回归“商标使用”的本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9月23日判决的HONDA案中,终于改变了自己十来年的立场,判决两被告的涉外定牌加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应当依据《商标法》做出整体一致的解释。如果当事人在生产制造或加工的产品上“以标注方式或其他方式使用了商标”,只要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就应当认定该使用状态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商品没有投入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没有实际接触该商品,就否认存在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而且,《商标法》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并不要求确实发生了混淆,而仅指如果接触到有可能发生混淆。
起点商标作为专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产交易信息请点击 【在线咨询】或添加微信 【19522093243】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与客服一对一沟通,为大家解决相关问题。
此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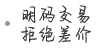
 商标分类
商标分类  商标转让
商标转让 






